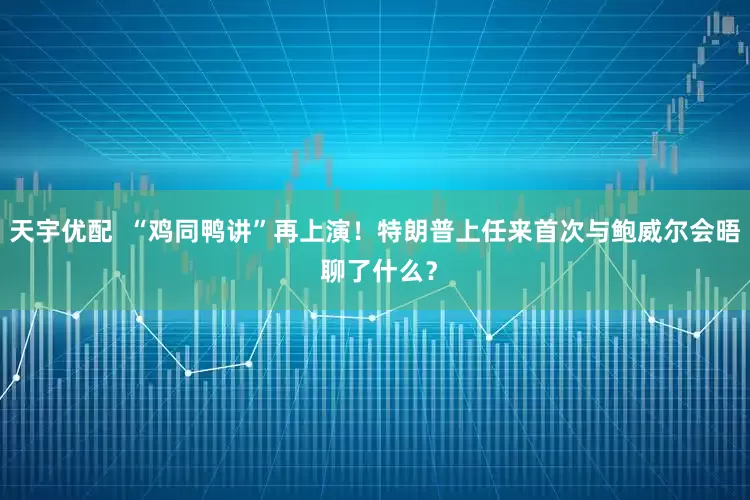亲情与尊严倍顺网倍顺网
门铃急促地响起,那种老式的"叮咚"声,在我这套复式楼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放下手中的账本,迟疑着打开门,竟是十年未见的小姨王秀兰,满面笑容地抱着一堆礼品站在门口。
"侄子,这些年过得好吗?你小姨来看你了!"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尖细,只是鬓角的白发让我恍然意识到岁月的流逝。
我叫陈家宝,今年四十有二,是城东最大的连锁超市"家宝生活"的老板。这个名字是我给自己的鞭策,也是对过去苦日子的一种告别。
回想十年前,我还只是北方那家大型机械厂的一名下岗工人,揣着五千二百四十块钱的遣散费,站在厂门口不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活。那个时候,我们这些被称为"待业人员"的人,像断了线的风筝,在改革的风口中摇摇欲坠。
我让小姨进门,她手里提着几个塑料袋,袋子上还印着她们县城百货大楼的标志。那种塑料袋我很熟悉,小时候能得到一个这样的袋子,都会像得了宝贝似的攒起来。
"家宝,你瞧我带了什么来?老家的腊肉、自家做的豆腐乳,还有这是你最爱吃的麻糖。"小姨放下食品袋,熟门熟路地走进我家客厅,好像她常来一样。
其实自从我结婚后,小姨就再没踏进过我家门。那是九十年代末,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,我和几十万工人一样成了社会的"多余人"。那时妻子李巧云刚刚怀上孩子,日子像寒冬里的小河一样冻得死死的。
家人们聚在一起商量我的婚事,想着是不是该往后推一推。小姨当时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——"巧云啊,你可想好了,跟着家宝这样一个下岗工人,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,以后的日子怎么过?现在城里多少有正式编制的小伙子排着队要娶你呢!"

我家的房子是五年前买的,一百六十平方的复式楼,装修不算豪华但很实用。客厅里那台29寸的彩色电视机,是我们这个小区最早安装有线电视的几户之一。茶几上摆着几本《农家致富》杂志,那是我创业初期的"宝贝",舍不得丢。
小姨坐在沙发上,打量着屋内的摆设,眼中闪烁着我读不懂的光芒。她的目光从墙上我和巧云的结婚照掠过,又在书架上那个红木相框上停留了一会儿——那是我母亲的遗照。
"家宝啊,你这日子过得真不错,听说你的超市都开了好几家了?"小姨啜饮着茶水,那茶是西湖龙井,是去年一个浙江的供货商送的。小姨从没喝过这么好的茶,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茶杯,好像害怕把它打碎。
"嗯,现在城里有九家,郊区两家。"我简单地回答,没有多说。创业的艰辛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,那种从绝望到希望的心路历程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
"家宝,你小姨我最近有点困难..."她放下茶杯,声音突然低了下来,像是打翻了五味瓶,又酸又涩。
果然,寒暄不过三句,小姨道出了此行目的——她想借二十八万元帮她在县城开个小超市。"现在县城发展得多快啊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冰箱,小超市肯定赚钱。"小姨说着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,显得年轻了许多。
我心里苦笑。超市哪有她想的那么好做?记得刚下岗那会儿,我也是被人家一忽悠,拿着全部积蓄去进了一批"紧俏货",结果发现那批日用品是滞销货,囤了半年都没卖出去,亏得只剩下裤衩。

我的超市是如何起步的?那是九八年的冬天,最冷的时候,我和巧云卖掉了单位分的福利房,凑了十万元本钱,在居民区外租了个小店面,还记得房东收了三千块钱的"好处费",说是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,怕吵到别人。
白天,我们卖米面油盐;晚上,我们就睡在店后面的小仓库里,一张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折叠床,一个单位发的老式电热锅,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。巧云生孩子那天,我正在用自行车送货,等赶到医院,孩子都已经满月般大小了。
"听说你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?"我岔开话题,问小姨。看到她提起儿子时眼里的光芒,我忽然明白了她今天来的真正目的。
"对呀,考上了省重点,计算机专业。"小姨的眼里闪过一丝自豪,随即又黯淡下来,"可惜学费太贵了,一年下来要五万多,加上住宿生活费...家宝,你是不知道,现在娃娃上学多贵啊!"
听着小姨絮絮叨叨地说着,我端起茶杯,思绪飘回了更远的过去。父亲在我十岁那年出了意外,是小姨接济过我和母亲。那时候,每逢过年,小姨都会给我带一身新衣服,有时还塞给我几块钱买糖吃。
"姨,你记不记得我小学六年级那年倍顺网,妈得了肺炎,是你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医院的?"我突然问道。那一年,母亲病重,是小姨四处借钱给母亲治病。医院里的走廊上,小姨抱着我,告诉我:"家宝,咱们家没有弱者,你要坚强。"
小姨的眼圈一下子红了:"那时候不是我帮你,还能有谁帮你?你姨夫那人,你也知道,嘴上不饶人,可心里是真疼你。"她说着,从包里掏出一张旧照片,那是我小学毕业时和她的合影,我瘦小的身体站在她身边,露出腼腆的笑容。

巧云端来水果从厨房出来,看见小姨手里的照片,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。她默默放下果盘,冲我使了个眼色,进了卧室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那年我们结婚前,小姨在亲戚面前数落我:"巧云家在棉纺厂当会计,条件是不错,可跟着家宝这穷小子,是要吃苦的。听说她父母都不同意呢!"这话伤了我的自尊,更伤了巧云的心。实际上,巧云父母对我很好,从没嫌弃过我的家境。
结婚那天,小姨送了一个红包,里面只有八十八块钱。要知道,那时候一般的红包都是两百起步,小姨这个数额,让我和巧云都感到脸上无光。婚礼上,小姨还对巧云说:"嫁给家宝,你以后啊,就是跟着吃苦了。"巧云当时就红了眼眶。
我和巧云的超市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。刚开业那会儿,邻居们都笑话我们:"现在国营商店都开不下去了,你们小两口还想做生意?"但我们硬是挺了过来。
多少个夜晚,巧云挺着大肚子坐在煤油灯下算账,那时候电费贵,我们省着用;多少个清晨,我们天不亮就骑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采购货物,常常是我踩着脚蹬,巧云在后面帮着推一把。
最难的是九九年那年,超市刚有点起色,一场大雨把仓库淹了,损失了近两万元的货物。那天晚上,我和巧云抱在一起哭了一场,然后擦干眼泪,第二天一早又去进货了。
"家宝,我知道你现在日子过得好,小姨有个想法..."小姨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我看着她,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亲戚面前嫌弃我的小姨,又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医院走廊上安慰我的小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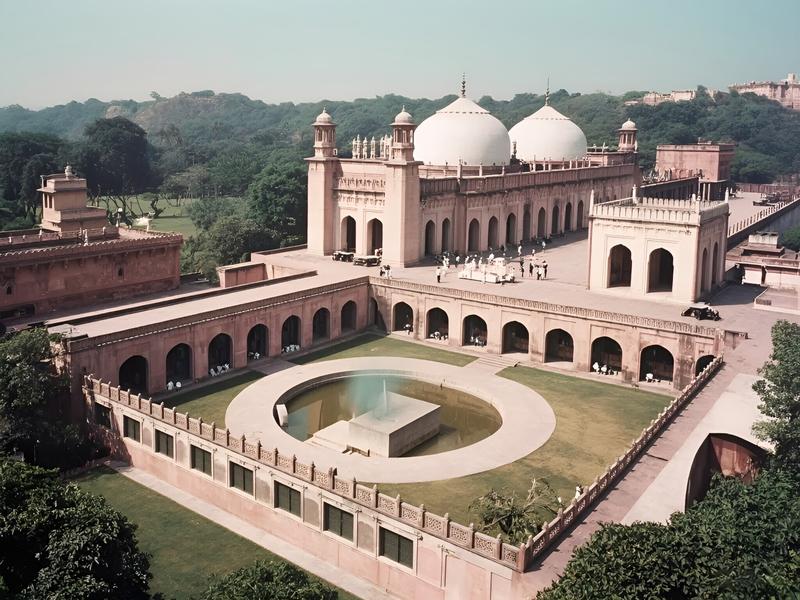
"小姨,您侄儿先把话说明白。"我斟酌着用词,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茶几,这是我紧张时的习惯。"侄儿念着您的养育之恩,明文的学费我全包了,四年二十万,我一次性给您。"
小姨的眼睛一亮,像是突然被点亮的灯泡。她连声道谢,嘴里念叨着"好侄子""有出息"之类的话,然后又小心翼翼地问:"那我开超市的事..."
"开超市不容易,我当年靠的是一步步摸索。"我拿出一个记事本,那是我创业初期用的,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的进货、销售和顾客反馈。"您看,这是我刚开始时的记录,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去批发市场,晚上十一点多才能休息。"
小姨翻看着我的记事本,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凝重。"这么辛苦啊?"她喃喃道。
"与其您重走这条路,不如我今年在您那县城开一家连锁店,您和姨夫可以去店里做管理,月薪五千起,怎么样?"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这也是我早就考虑过的扩张计划。
小姨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。她大概没想到,昔日那个需要她接济的侄子,如今已经成长为能够给她安排工作的人。那种角色转变的微妙,让我们两个人都有些不适应。
"家宝,你是嫌小姨我没本事吗?"她的声音有些颤抖,自尊心被触动了。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,最看重的就是面子和尊严。
"不是的,小姨,我是为您着想。"我解释道,"开超市真的很辛苦,特别是前几年,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您和姨夫年纪大了,吃不消的。再说,明文还在上学,需要人照顾...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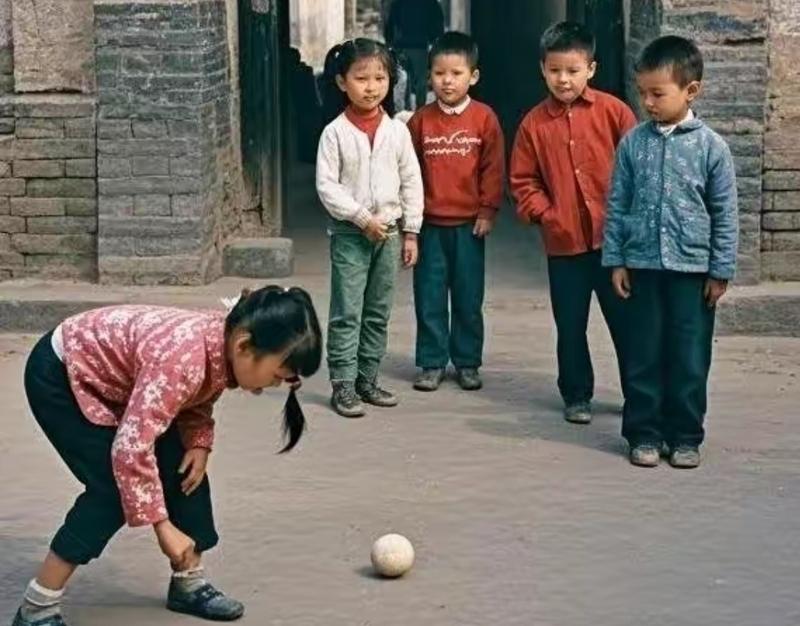
提起儿子,小姨的态度又软化了。她沉默了好一会儿,眼圈微红:"家宝,小姨当年...是有些势利了。那时候看你下岗,又是单亲家庭,怕巧云跟着你吃苦..."
我摆摆手:"小姨,人都有难处。您当年关心我和母亲,如今我有能力了,自然也该回报。只是二十八万创业,我真不建议。您和姨夫年纪也大了,不如踏实工作几年,等明文毕业了,他自己有能力创业。"
巧云从卧室出来,带着我们的儿子小强。今年小强上初二了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已经比巧云高出半个头。他怯生生地喊了声:"小姨好。"
小姨的眼睛一亮,上前摸了摸小强的头:"哎呀,小强都这么大了,真像你爸爸小时候!"她从包里又掏出一个红包,塞给小强:"拿着,姨给你的零花钱。"
小强看了我一眼,我点点头,他才接过红包,乖巧地道谢。巧云在一旁冷眼旁观倍顺网,没有说话。我知道她心里还有疙瘩,当年小姨的话伤得她不轻。
小姨留下来吃了晚饭。饭桌上,她一直夸赞巧云的手艺好,说比外面饭店做的还香。巧云只是淡淡地笑,没有多说什么。饭后,小姨特意拉着巧云的手,低声说了些什么,我看见巧云的表情缓和了许多。
送小姨离开时,我把准备好的信封塞给她:"这是给明文的学费和生活费,够他大学四年用的了。"小姨接过信封,手有些发抖,好像那不是钱,而是一块烫手的烙铁。
"家宝,小姨..."她欲言又止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"小姨,您当年对我和妈的帮助,我都记在心里。"我拍拍她的肩膀,"这不是施舍,是亲情。"
小姨突然抓住我的手:"家宝,对不起,那年你结婚,我...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。巧云是个好姑娘,是我有眼无珠。"

我笑笑:"小姨,都过去了。人都会变的,您看我,从一个下岗工人变成了超市老板;您也从一个乡村妇女变成了即将有大学生儿子的母亲。"
小姨擦擦眼泪:"家宝,你和巧云真的很了不起。当年你们刚开小店那会儿,我回老家还跟大家伙说,我侄子媳妇嫁不好,跟着下岗工人受苦去了...现在想想,我真是..."
"小姨,没事。"我打断她的话,"您去给明文交学费吧,让他好好学习。至于超市的事,我过段时间去县城看看,找个合适的店面,到时候您和姨夫来帮忙。"
小姨点点头,眼神里有感激,也有一丝释然。她站在楼下,突然显得有些佝偻,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高大的小姨了。
回到家,巧云正在厨房洗碗。我从背后抱住她:"小姨跟你说什么了?"
巧云转过身,靠在我怀里:"她向我道歉了,说当年不该那么说我们。她还说,看到我们现在的日子,她很高兴,也很自豪。"
我笑了:"你原谅她了?"
巧云点点头:"人都会变的。再说,她毕竟帮过你和妈妈。"她顿了顿,"你真的要给她侄子出学费?那可是二十万啊。"
"钱是身外物。"我摸摸巧云的头,"小姨有她的苦衷,当年要不是她,我和妈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"
巧云叹了口气:"我明白。只是有时候想想,人情这东西真难算清。当年她看不起你,现在又来找你帮忙..."
"那你说,我该怎么做?"我问她。
巧云想了想:"就按你说的做吧。帮明文出学费,在县城开家超市。说到底,是一家人。"

两个月后,我在小姨所在的县城开了第十二家连锁店。开业那天,县城下了一场小雨,却挡不住前来捧场的人群。小姨和姨夫都来了,站在收银台后面,笑得像两个孩子。
姨夫穿着我给他买的西装,看起来有些不自在,但眼神里满是骄傲。他对每一个进店的顾客都说:"这是我侄子的超市,全县最大的连锁店!"
开业典礼上,我特意请了县里的文艺队来表演,还准备了不少小礼品发给顾客。小姨在一旁忙前忙后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仿佛年轻了十岁。
晚上,我们一家人坐在小姨家的饭桌前。那是一张老式的方桌,上面还铺着塑料桌布,边角处已经有些发黄。小姨做了满桌子菜,有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。
"来,家宝,多吃点。"小姨给我夹菜,就像小时候一样,"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,记得吗?每次你来,我都会做这道菜。"
我点点头,嘴里塞满了肉,那熟悉的味道让我一下子回到了童年。对面的姨夫举起酒杯:"来,家宝,敬你一杯。你小时候我就说你有出息,果然没错!"
我笑着和他碰杯,心里明白,这话估计是现编的。但此刻,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我们坐在一起,像一家人一样吃饭,没有隔阂,没有芥蒂。
饭后,明文拿出他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看。那张红色的纸上,印着学校的名字和校徽,显得庄严而神圣。我记得我自己高中毕业后,因为家里条件不好,只能去了技校,从来没有机会摸到这样的录取通知书。
"家宝叔,谢谢你,"明文真诚地说,"我会好好学习,不辜负你的期望。"

我拍拍他的肩膀:"好好读书,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钱不是问题,叔叔能帮你的都会帮。"
小姨在一旁抹着眼泪,姨夫则拍着胸脯保证:"明文这孩子争气,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!"
回去的路上,巧云挽着我的手,小声问:"感觉怎么样?"
我深吸一口气,看着夜色中的县城街道,那些老式的建筑和新开的店铺并存,就像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。"挺好的,"我说,"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个心愿。"
巧云笑了:"你啊,就是心软。不过我喜欢你这样。"
我望着远处的灯火,忽然明白,岁月不仅改变了我,也改变了所有人。小姨从当年那个看不起下岗工人的刻薄亲戚,变成了今天这个感恩戴德的长辈;而我,从那个需要救济的孤儿,变成了能够给予帮助的人。
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途,我们都在路上不断地变化、成长,有时候迷失,有时候坚定。而亲情,则是那盏始终不灭的灯,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超市开业一周后,我接到小姨的电话,说生意很好,每天都有不少回头客。她在电话里笑着说:"家宝,小姨以前看走眼了,你真有本事!"
我笑笑没说话。成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是我和巧云一起打拼出来的。回想当初,如果不是巧云不顾家人反对嫁给我这个下岗工人,我可能早就被生活打垮了。
那天晚上,我和巧云坐在阳台上,看着城市的夜景,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。巧云靠在我肩上,轻声说:"家宝,你知道吗?当年我父母其实也不同意我嫁给你,说你家境不好,又没有正式工作,怕我跟着受苦。"
我愣了一下:"你从没告诉过我。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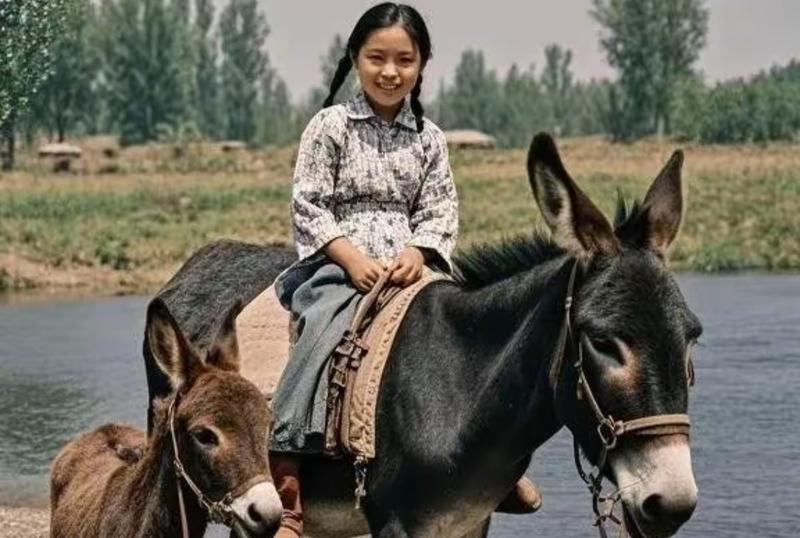
巧云笑了:"我怕你自卑啊。我当时就跟我爸妈说,家宝这个人虽然家境不好,但他勤劳、踏实、有想法,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。"
我紧紧抱住她:"谢谢你,巧云。没有你,就没有今天的我。"
巧云摸着我的脸:"傻瓜,咱们是一家人,哪来那么多谢谢。"
是啊,一家人。无论是小姨一家,还是我和巧云,我们都是被血脉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亲人。尊严很重要,但亲情同样珍贵。或许,生活的真谛就在于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。
半年后,小姨的超市已经步入正轨,明文也在大学里表现优异。我收到了明文寄来的一封信,信中他说要努力学习计算机技术,毕业后帮我开发一套超市管理系统,让我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好。
读完信,我笑了。这就是生活,有得有失,有苦有甜。当年的困境已经过去,而今天的成功来之不易。重要的是,我们没有忘记初心,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。
亲情与尊严,原来可以如此和谐地并存。
胜亿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